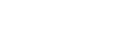他突然死了,和他突然不爱你了,你会选哪一个。
在越来越频繁梦到你的时候,看到这一句话,问我怎么选。
我想,我还是选二吧,我希望你好好活着。
昨天去医院,医院搬走了,我也没说什么,去逛了逛公园。
那是我们以前参加竞赛午休时候一起逛过的公园。现在成为了文物保护点,景区,但逛着逛着,我就说不出来话了。
这里,从分开后,我再也没来过,记忆里那些斑驳灰白的湖石,和一整片的深浅湖滩,是借着怕女生走不稳脚滑才有的牵手。手心的潮热还记忆犹新,但那片水域已经被隔开重构。堆砌着铁红色嶙峋的石头假山。关帝庙的石柱依旧红漆斑驳,但底色已经不再是枯败的黑木,而是苍白的水泥。泥塑也是鲜艳的,和我们那张被偷拍照片里的灰暗截然不同。那张被潮湿沁透晕染的旧照里,是我们隔着几人佯装结拜的偷瞄,你的校服是红黄,我的校服是蓝白,哪一件都艳过关帝爷的衣袍和脸。洗照片时候,因为这张过曝边角,本来是不洗的废片,是你偷偷回去加了两张,各自保存。去年整理照片,你的脸也看不清了,但我记得你的神态。我妈说,这张什么时候拍的,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去秋游啊,都花了,扔掉吧。我一时语噎,最后轻轻嗯了一声。然后在晚上去扔垃圾时候,又从垃圾袋里翻出来,不停的擦,擦着擦着眼泪就止不住了。
从公园回来,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它面目全非,我找不到一点,我们回忆的痕迹。没有答案,心里空的像被抽过真空的水,那些空话套话的爆沸之后,结冰了,也没办再思考,那些理由是空的,我的心是冰冻的。
昨晚又梦到你了,在青春懵懂的年纪,我们最大的尺度是拥抱和牵手,最常干的是解题写信。
但昨晚,你带着我,从简单的婚礼上一路飞奔过很多风景。你是黑色的西装白衬衫,我是简单的白裙。我们路过的风景,是我们曾经的同学老师,和当年集体结拜一样,他们也和年少的恋人在不同的场景里,结婚。我们第一次以恋人的姿态,路过他们的风景。我们见证过他们的幸福甜蜜,也向他展示我们的美好。
我们从那个公园出发,路过母校的情人坡,这里是我们曾经带着红袖章借着检查为名,翘掉午间操闲谈的地方。
又路过其他学校考场的表白墙,这里有那张照片的中心人物的婚礼。新郎是我们的同学,新娘是当时陪他去考试的别的学校女生。新郎被捉弄他的伴娘团隔着表白墙的栅栏门要婚戒,他着急的找不到,向我们借。你低头看我,我们两个才恍然我们结婚什么都没有,然后别人起哄,你拿出你家的钥匙,拆了圈给我套在手指上,然后让我把另一个套在你的手指上,两个人像傻子一样,看着月光下闪着银白色的钢圈傻笑,然后我流着泪,被你牵着飞快跑走。那个被围困的新郎,大骂秀恩爱死的快是我们离开的背景乐。
我不知道我为什哭,我一直在哭,你一直在笑,是我最喜欢的斯文秀气笑容。我知道我是开心的,非常非常开心,但又知道我的眼泪是伤心的,非常非常伤心。你始终温和,一边说我,为什么变得这么爱哭,明明是女汉子来着,怎么这么多年过去变成小泪包了。
然后像说错话一样愣住了,说,箬箬,这么多年,我还是一样爱你,无论你变成什么样。
这时候我们突然来到天文台,这是我们去参加省赛时候,两个学校联谊一起去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是白天,但梦里是晚上,满天星光。你低头给我擦眼泪,手指还是少年的修长骨感,脱了黑色的西装给我披上,就像那年假借跑出汗了把你的校服给我一样。
在你低头凑近要亲一个哭包时候,我醒了。
醒来我是笑得,但枕头是湿的。笑着笑着,泪水就像洪水一样,无声但汹涌而出。
我甚至气自己,为什么不再多梦一会儿,毕竟,我们没接过吻。
我看过这个问题很多次,我一如既往的选择二,你有你的健康幸福就好。
在开始一段感情时候,我真的想过放下,所以我默许了妈妈扔掉唯一一张合照。但我始终放不下,所以我又偷偷把照片捡回来。
有些感情,就像老砖墙上潮湿开出来的霉花,可以涂抹,可以遮盖,可以辐照,表面可以什么都不存在。但内里,我的心,早被霉菌的根系生长侵蚀得酥松绵软,风吹一下,湮寂归尘。
我曾以为,有些人是礼物,是弥补,但不是。就像梦里的清醒一样,我清楚得知道,云泥之别,感情没有平替,人也没有。
有人说,每次梦里相遇都是散缘,你是不是,真的不爱我了?还是,你要有新的开始了?所以才在梦里补我一个婚礼?我不想缘尽,我也不想缘灭,我没有你想的勇敢,没有,放我一个人,你会担心的。
我们没有惊心动魄,没有抵死缠绵,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逾矩越规,我不懂,那些青春懵懂的分不清好感和爱的时候怎么认定了彼此,怎么在几年里发酵到满心欢喜,怎么在两个早熟的灵魂了知道彼此的契合,怎么能在未来的规划里全是彼此。
你永远不知道,我知道你手机里播放最多的是我五音不全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我有多崩溃,我甚至无法接受我们有那么多默契的约定,却从来没被任何人祝福过有多怨念。当年为隐秘沾沾自喜,现在为隐秘肝肠寸断。
我相信爱情,因为我曾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