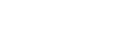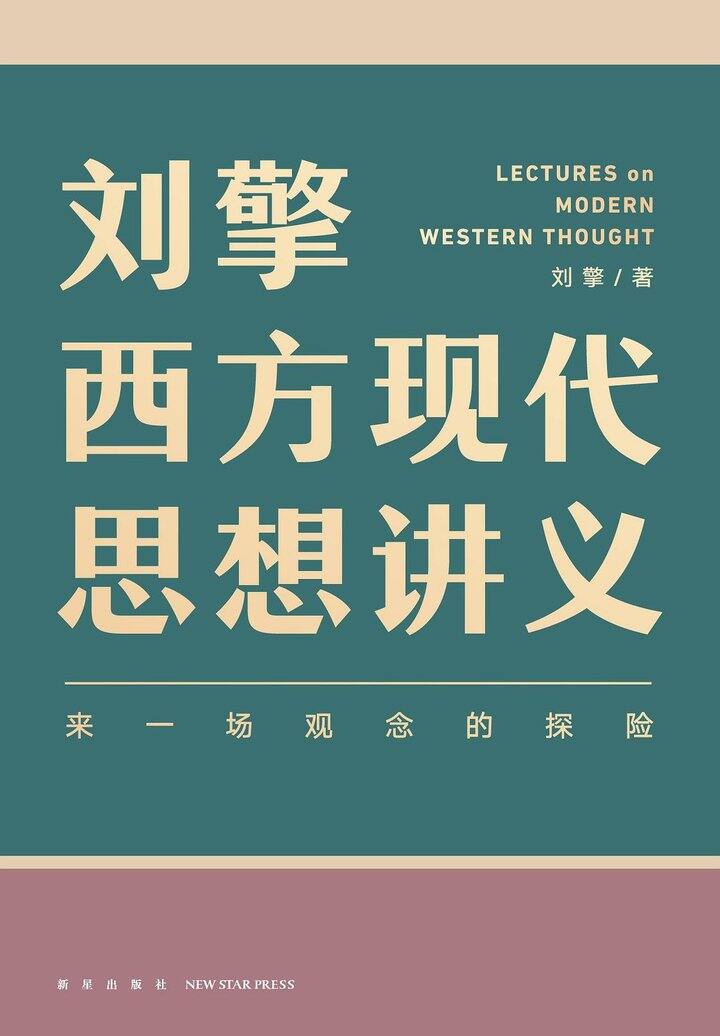 > 恰恰是因为明白了每个人的视角都只是视角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眼中的真相并不是绝对的真相。了解到不同视角中有着不同的真相,不是要让我们去和他人划清界限,而是邀请我们对更多的视角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倾听、理解和学习它们。 ……视角主义教给我们的,不是分裂的必然,而是谦逊的必要。
> 恰恰是因为明白了每个人的视角都只是视角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眼中的真相并不是绝对的真相。了解到不同视角中有着不同的真相,不是要让我们去和他人划清界限,而是邀请我们对更多的视角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倾听、理解和学习它们。 ……视角主义教给我们的,不是分裂的必然,而是谦逊的必要。>虚无这个真相并不直接导致消极。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不存在的奖杯。如果你相信了这种虚幻的信念,那么虚无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 ,你就会感到悲观绝望。这就是消极的虚无主义。 但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么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县区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
>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止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
>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到最后要么是受虐,在羞耻中享受快乐;要么是施虐,在内疚中感到愉悦。
>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
>人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以称为真正的成年?我认为大概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一个人成年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开始自觉的自我反思:你不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有意识地反观自省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