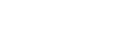(亲们,我来刷屏了~!把漏掉的补上,赶上澄文的进度,算送给亲们的新年礼物哈~这一章是爱情啊,自己很喜欢这些与爱情有关的片段,冬天真得好冷,有爱才温暖,愿《久离欢》的读者们,2015有爱相随,顺遂愉悦~)
书宵在一旁扶住她低声道:“娘娘,只有这个办法,才可保你和公子的周全。”
重允看着一波澄碧的泉水,一步步走了下去,越走越深,温泉水漫过他的膝盖,漫过他的腰,漫过他的胸口,漫过他的脖颈,他一步一步走得很稳,虽然走得有些慢却并无半分迟疑,温泉水最终漫过了他的头顶。
姜姬俯在池边用短刀划破手腕将鲜血洒入池中,在池边扭动四肢,闭目念咒。泉水顿时沸反盈天如煮沸的开水,泛起汩汩水泡蒸腾起大量水汽,池底传来重允痛苦的吼叫,如同困兽。姜姬趴在池边,绝望地盯着池底嘴唇发抖尖利道:“允儿,允儿你怎么样?”泉水沸腾了一刻后渐渐平息,重允的吼叫声越来越微弱直至彻底平息。
澄碧泉水下漂浮起两个身影,一个是重允,他面无表情地睁着眼,一个是凛君,他上身赤裸,胸口有一个窟窿,凛君面无人色,没有气息,同样面无表情地睁着眼,突然,重允和凛君的眼睛同时眨了一下,猛地站了起来。
重允举起手,凛君也举起手,重允转动头,凛君也转动头,书宵进到温泉把重允扶了上来道:“娘娘用驭鬼术把你与大王的神思凝结在一起,他死了,你便是他,你想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但在最初三日,他只能重复你动作,三日后神思完全交融,方能按照你所想来说话,行动。不过公子还是注意尽量不要和大王同时出场,或者距离隔远一些,以免被人看出端倪。”
重允沉默着点了下头。
姜姬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她看着重允声音清冷道:“这三日就留在甘泉宫,对外称我病了,等到能完全操纵他后你再回去。”
她又看着书宵道:“带允儿去换身干净衣服,把昏睡术解了,让宫人收拾好院子不得擅自走动,没我吩咐谁都不许进来。”
书宵带着重允走了,重允到最后也没和姜姬说一句话。我看出,这个少年看向他母亲的眼光已不似从前。
姜姬握着一块锦帕,擦拭凛君脸上的水珠,锦帕抚上他龙姿日角的额头,按上他高高的鼻梁,摩挲那张经常逗弄她又爱吻她的嘴,锦帕从颤抖的手中滑落,她心痛得无法呼吸,凛君,她抱着他的头哭了起来,凛君,对不起,对不起,凛君,我爱你,我爱你,凛君。
她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不断对他说,对不起,我爱你。直到太累了伏在他腿上睡了过去,她多希望这是一场梦,梦醒后凛君温热的大手放在她背上,依然温言唤她“阿妩。”
深夜她醒来,面前的凛君阖着眼,仿佛睡着了一般,她的目光往下移动,他胸口上的窟窿在黯淡月光下触目惊心。
终究是真的。
她偎在他身旁想到了重允,在重允继承大统之前,事情还没结束。她起身拿起短刀,向古槐走去,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黄色槐叶被大风吹落枝头,在冷寂的秋夜瑟瑟飘零,西风在静谧的深夜吹响槐叶,似一曲悲伤的挽歌。
姜姬单薄的身影行在秋风渐重的夜晚,落叶拂了她一身,她在古槐下挖出一个小坑,将短刀放入坑中埋在树下,她似乎做了一个决定,对着古槐喃喃自语,我走近了竖着耳朵听,却什么也听不到,不大对劲,连风的声音也消失了,一切声音都消失了,画面开始褪色,如同融化的白雪从我面前消褪。
糟了,出事了。
我眼前一花,头晕目眩,缓过神来时,一种颠簸感颠得我七晕八素。我努力睁眼发现自己正被离殃扛在肩上飞奔。
“怎么回事唉?”
离殃一路疾跑小声道:“有人来了,是个狠角,施昏睡术对她没用,师姐你赶紧走,被逮到就麻烦了。”
我心想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好的不灵坏的灵,我对离殃道:“是书宵,你自己当心点,赶快回房,别让她看出破绽。”
离殃一把将我扔过墙头说了声“好!”
我便听到他的脚步飞快离去。
这小子,跑得倒真快,临危逃命是一把好手。我正发着感慨突然发现不对头,他一把将我扔过墙头自己跑了,谁来接住我啊?!
我身子在空中快速下坠,惊慌失措却也没有办法,最后闭上眼,想这回高处坠落至少得在床上躺三天,又是私自行动不能算工伤,还要编一个梦游从楼上摔下来的借口,显得自己特别二,真是倒霉极了。
我一边自怨自艾,一边倒数还有两秒就要砸到地上,突然被一双手牢牢接住,我最终砸进一个人怀里,他怀里有股熟悉好闻的男子气息,我猛然睁开眼,就看到月光下亓麟清朗至极的侧脸,他接住我脚步不停,快速向一条小巷走去,七弯八拐了好一阵,直到一座山前,才停了下来,低头问:“还要再抱一会儿?”
我从惊心动魄的逃命现场缓过神来,看到自己被他这样抱在怀中,登时大窘,手忙脚乱地跳下来,连连道:“不用了,不用了,抱一下就可以了。”
愣了下觉得不大对劲,侧着头看着他问:“你怎么在这儿?”
他悠然抬手整了下被我抓皱的衣襟道:“散步啊。”
我看着他扯这种毫无诚意的谎真是无语,半夜三更他吃饱撑得,从南宫跑到甘泉宫来散步。
他好像看透我心思,又悠然补充了一句:“今晚吃得比较多,多走了几步,正好碰到离国手从墙内飞出来,不知你是在做什么?”
我张了嘴,呆了两秒,看到手里的碧桐灵光一闪,竖起手指道:“练功!”
他抱着胳膊,支着下巴,看着我感叹道:“真是神功啊,都会飞了。”
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干笑一声:“天下武功无奇不有,会飞也算不得什么。借问一下,东宫怎么走?”
他指着身后那座山:“翻过红叶山,从小道下去就是了。”
我看着身后高耸漆黑的红叶山,心中渗得慌,缩了下脖子问:“还有别的路吗?”
他淡淡道:“有,你再从甘泉宫门口过也能回去,怎么来怎么回。”
我哪里还敢从甘泉宫过,万一书宵在那儿,不是把我逮个正着,可这黑黝黝的红叶山也太吓人了。
正在纠结中,亓麟已迈脚往上山的小道走去,我紧紧跟着他问:“你要爬山?”
他“嗯”了一声,我奇怪道:“你半夜三更来爬山?”
他伸展了一下胳膊:“爬爬山更有助于消化。你可以跟着我走,或者原路返回。”
说完向山上走去,我拎着碧桐,提着裙踞,别无选择地跟随他脚步上了山。
进了山才发现,其实山里也不像外面看上去那么漆黑,有月光射进深林,照在松间,清泉在山石上流动,闪着粼粼的水光,万籁俱寂的山林,有一股幽深的禅意。
这种宁静的氛围在无形中缓解了我方才读心后,内心的压抑,姜姬这一段往事,真是苦涩,她爱的人被凛君所杀,她杀了凛君却发现自己已爱上他。
读心时我被她情绪带着,感受着她每一缕心绪,每一丝痛苦,入戏很深,被重重虐了一道,心意沉沉。
姜姬和景王的这一段相爱相杀,真不是一般的悲剧。爱情是如此珍稀的东西,天时、地利、人和一点都不能错,一有过错,便会错过。
如果凛君在尾千之前遇到姜姬,会不会就是不同结局?如果凛君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禽兽,会不会他死了反而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只是世间事,向来很难如人意,你永远不知道命运会在哪个岔口,把你导上另一条路,那条路上的风景,不是你能想象到的。这是一个婆娑的世界,婆娑既遗憾。
联想到我和亓麟,在关外他对我有意时,我不知道,待我知道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时,他去了乌桑,等我去乌桑找到他,他又成了我妹夫,最后知道是个误会,他已为我舍了性命。待我在景国与他重逢,他已然忘了我,等我想方设法接近他,试图让他记起我时,他又有了别的女人。
这一番算下来我们被命运那只翻云覆雨手折腾了三四番,天时、地利、人和全都错,一段情缘上写满了饱含血泪的错过二字。
今晚的我,感触良多,作为一个粗线条的女汉子,我突然萌发出找人谈心的冲动,我看着前方的亓麟,很想跟他探讨下对爱情的看法,反正我已经问过他不少奇奇怪怪的问题,也不在乎多问几个,想到这儿,我清了下嗓子道:“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值此良夜,不如聊天。”
亓麟淡淡道:“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哽了一下道:“我想与公子探讨下关于爱情的话题。”
他脚步顿了下,淡淡道:“爱情?那可是很复杂的。”
我拍了一下手道:“我也觉得好复杂,所以想和你聊一聊,我,我有个朋友,她,她喜欢一个人,但是她和那个人好像很没有缘分,总是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事错过,你说像这样的情况,她究竟是应该坚持还是应该放弃了?”
他停了步子,侧过身看着我笑道:“那要看你,哦,你那个朋友,遇到的是什么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说完继续向山上走,我跟着后面一边爬山一边气喘吁吁道:“这个,就是她喜欢的那个人,那个人现在,现在有了别的女人,按理,按理说她应该放弃算了,可心里,心里总有些舍,舍不得。你觉得,觉得她,应该,应该怎么办?”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这段话觉得之前提议一边爬山一边聊天的我真是个神经病。
他又停下步子,回身看着按着腰大口喘气的我问:“你的朋友很喜欢那个人?”
我看着他月色里清朗至极的脸,微愣地垂下眼,点了点头,我的脸一定红了,好在光线不好,他不会看到。
他继续问道:“你朋友喜欢的那个人现在的女人有没有你朋友那样喜欢那个人?”
我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搞明白他的意思是,胡小仙有没有我这样喜欢亓麟。我坚定摇头道:“没有。那个女人,不会比我朋友更喜欢他。”
他淡淡问:“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想起以前的种种,又开始难过,低声道:“因为我的这个朋友,把他看得很珍重,她很倒霉,国破家亡还毁容失魂,那个人,是她努力活下去最为坚韧的希望。”
我看着头顶上皎洁的弯月,轻声道:“她还设想了很多种未来,像可以开绣庄,可以混江湖,可以开客栈,让他选一种他喜欢的,一起去将梦想实现。她想象里的未来,从来不能没有他。”
他静静看着我,半响没有说话,那双漆黑的眸子深沉得吸附进所有光亮。他伸出手,摘下落在我头顶的一枚火红槭叶,将小小火红的槭叶别在我耳畔,淡淡道:“那就把他抢回来。”
随后回身继续往上走,我愣在原地,受到了极大的启发,那簇被压制在心底的微弱火苗,又开始灼灼闪动。亓麟,连你都觉得我应该把你抢回来?
我加紧两步赶上他巴巴儿问道:“应该怎么抢了?你能不能教教我?”
他按着额头,显得很伤神:“你就不能自己发挥下想象力?”
此时我们已经爬上山顶,前方传来淙淙水声好像是个水潭,我一边走一边冥思苦想道:“扮娇弱有没有用啊?我看男的好像都挺吃这一套啊。”
正走着,脚下一滑,左脚狠狠扭了一下,“嘶!”我倒抽一口冷气,蹲下身来,只一小会儿左脚已肿得像个馒头。
亓麟在前面昂着头走,我急忙喊道:“喂!我把脚扭了!”
他回头看着我笑了下道:“扮得不错,继续练。”随后继续前行绕过一个弯儿就不见了。
我欲哭无泪地在蹲在地上狂喊:“喂!是真的呀,我真的把脚扭了!你别走啊,你走了我怎么办!”
喊了半天也没人搭理我,深夜的深山老林,除了月光可以照到的视线,往四周看都是黑黝黝的,一阵凉风吹过,激得我全身汗毛倒竖,我努力站起身,颤悠悠挪动一下腿,妈呀,疼死了!我呜地又蹲下身,想了想,觉得只能爬下山了。
于是很凄惨地伏在地上,将碧桐背在背上,左右手肘交互地往前爬,这个点儿如果有人打这儿过,一定会被我吓死。
我满心怨愤地在地上爬,心想那个混蛋,怎么跑得那么快,说走就走,就一点儿不担心我吗?
我怨念地爬着,眼前突然出现光亮,光亮里有一袭绣云纹的玄黑衣角停在面前,我顺着衣角向上看,就看到亓麟在我头顶提了一草笼流萤,梦幻般萤火中映照出他清朗至极的脸,他微皱了眉道:“真扭了?”
我哀号道:“废话,我都爬了半天了,你跑哪儿去了?”
他淡淡道:“去捉了一笼流萤,方便照路。”皱着眉蹲下身,轻轻捏了下我左脚,我疼得又“嘶”地一声倒抽冷气。
“肿得这么厉害,要赶紧回去敷药。”他皱着眉说完,拍拍自己肩膀道:“趴上来。”
“嗯?”我有些惊疑。
他回头看着我道:“或者你就继续在这儿爬,爬到明天中午应该也能下山。”
我听了赶紧趴到他背上,双手紧紧环在他胸前,生怕他甩了我自己走了。
他轻轻笑了下,将忘忧草编织的装着流萤的草笼递到我手中,反剪了手兜住我,站起身,背着我往山下走。
我伏在他背上举着萤火为他照明,鼻端呼吸的是他身上清冽似柠檬的气息,耳边听到的是他强劲却略有些快的心跳,他走得不徐不疾,步子很稳,但隔着衣服我还是觉得他好像有些热,他一热,连带着趴在他背上的我也开始热,我很不好意思地想到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话,努力抬起上身,让自己不要趴得那么紧。
正在我挣扎着向上昂起身子时,他淡淡问道:“离国手最近是不是心情比较不错,心胸比较开阔?”
心胸开阔?如果心胸不开阔,遇到那么多倒霉催的事儿,我早抑郁死了。
心情不错?好像也还可以吧。
我昂着身子“嗯”了一声,问道:“为什么问这个?”
他淡淡道:“有个词叫心宽体胖,你的情况很符合。”
我猛地明白过来他是在嫌我重,顿觉难堪,转念一想他心跳加快身体发热估计也是被我的体重给压出来的,更加羞愤欲死。
这个混蛋,就是这么毒舌,连暗示都懒得想,直接明示,完全不在乎伏在他背上的我的心情。
我顿生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全然没了方才矜持羞涩的情态,冷冷道:“公子没事也多锻炼下,连个女人都背不动,倒叫人笑话。”
他笑了一声,微侧头狡黠地瞟了我一眼道:“你说得对,那便好好趴着,给在下一个负重锻炼的机会。”
我很配合地狠狠压到他背上,心中默念:“碾死你!”
他兜着我的手紧了紧,向上耸了下,让我趴得更稳当,随后悠然地继续前行。
子夜月色下的红叶山,枫红似火,手掌般的叶片在风中哗哗拍响,山石台阶上铺满青紫艳红的落叶,长长一道锦绣旖旎。
我盯着伸展的右手上挑着的那笼萤火,它梦幻般的光芒照着两步之内的山路,我置身这个场景,看着黄绿的温柔光芒,觉得真像是一个梦。
陈留国七夕的那袋萤火,落霞浦独揽的月下萤火,和我右手中忘忧草笼住的萤火,叠加到一起,清晰映照着亓麟清朗至极的侧脸,风月正好,萤火正亮,他背着我行在冷寂的山道上,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我伏在他背上,听着他的心跳,说不出的安心,他身上传来熟悉清冽的气息,让我昏沉欲睡,我迷蒙地想着这条路可不可以再漫长一点?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他似乎感觉到我要睡,开始同我说话:“你今日运气不错,秋日流萤一般很难遇到。”
我“哦?”了一声,打起精神,竖起耳朵。
他慢慢道:“流萤会用一个夏日的时间去寻找自己的伴侣,如果没找到,也会因为想爱的力量,撑过夏日变成秋日流萤,继续寻觅直至找到伴侣,传说遇到秋日流萤,愿望就能成真。”
愿望啊,迎着凉风我心匪然,我的愿望无非就是你呵,我趴在他背上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对着眼前的流萤虔诚地默默许愿“流萤啊,流萤,请让我能与亓麟再续前缘。”
亓麟声音幽幽响起:“离国手可以下山了再许愿么?看不清路了。”
……
最后他将我背回啼霜阁,寻药给我涂上,说了声“再会。”便翻墙走了,我恋恋不舍地看着他翻墙离去的潇洒身姿,我喜欢的人,翻墙都翻得那么帅,真是要命。
我躺在床上,把忘忧草笼着的流萤小心放在枕边,看着这捧梦幻萤光,想着自己的愿望,忘忧草清淡的香气缓缓将我绕入梦乡,我闻着这让人忘忧的草香,想着心事,对着萤火沉沉入睡,一夜好眠。
因着扭了脚,我在房内歇了三天,歇到第四天终于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歇下去。扭脚固然不便,但我不积极地去读心,也有我自己的因素,自从那晚潜入姜姬房内,在她睡梦中对她读心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竟有些不知该如何面对这对母子。
这个事情根本不会有好结果,最后不是重允杀了自己母亲,就是姜姬杀了自己儿子。姜姬很苦,坚持到今天不容易,她已经被逼无奈弑夫,难道最后还要被逼无奈弑子?重允也不容易,三年前的重阳,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杀了父亲,一夜之间明白真相,知道自己是个野种。从景国公子跌落到野种,这个落差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他承受了下来,还用驭鬼术操纵凛君,成为幕后的景王。
这三年在他操纵下的景国,国力大增,内政外交周密布局,内政上知人会用,能谋善断,外交上远交近攻,韬光养晦。他做得比凛君还要好,谁又能想得到,这个让天下敬畏三分的霸主景王,其实只是个十一岁的少年。